作者:苏新华
在中国地震史上,迄今为止,唐山地震是唯一在震前有地震工作者追踪震情奔赴现场并在地震极震区殉职的一次地震。当时,在全国的地震队伍中,专程赶去唐山的就是河北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的六名地震工作者,最后六人小组在唐山极震区全部以身殉职。
这六人小组带队的组长苏英俊,是我的父亲。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把我所知道的关于父亲赴唐山前前后后的真实情况如实地写下来,这不仅仅是追思,也是一种反思。
—————————-
(续前)
(八)京津(唐渤张)大震要求成功预报?!
现在说说北京方面,国家地震局。
国家地震局是国务院直属单位。那个年代,科研单位的一把手往往只是旗杆作用,不说也罢。当时副局长查志远可说是国家地震局地震预报业务的实际负责人,梅世蓉作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主管华北震情。他们两个人都属于地震预报决策层,从他们的履历看,两人都为我国地震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过贡献。特别是海城地震预报,梅世蓉立过功,她当时也是主管华北震情,曾受到过国务院领导的接见。
海城地震成功预报之后,全国的舆论宣传铺天盖地。报道称,海城地震的预报成功开创了人类预报地震的先河,国外没有做到,中国做到了。当时全国上下欢欣鼓舞、热血沸腾,要比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振奋百倍。那个时候,我国处在文革后期,仍然没有脱离“粮食亩产过万斤”的时代。国家领导人还真以为我国解决了准确预报大震的世界难题。
牛皮吹大了,压力就来了。
查志远后来回忆时说:“华国锋在海城地震后不久就向国家地震局口头提出了‘京津地区要做到二十四小时前报出五级以上地震’的要求……京津地区凡是五级以上的地震都要做到成功预报,这是中央国务院给地震工作下达的硬指标。” (摘自查志远回忆录《我们为什么未能预报唐山地震》,刊登于香港明报月刊2006年8月号)
唐山行政隶属河北省管辖,但在地震地质图上,唐山落在了北京所在的板块上,京津唐是一体,属于同一个地震带。其实,唐山离北京并不近,直线距离都长达160公里了。
在父亲的遗物中有一本印刷体资料,是河北省地震办公室翻印的,上面有国家地震预报条例的简单说明,其中写着,“为了防止阶级敌人造谣破坏,除中央及省委有权发布地震预报消息外,其他部门包括地震专业台站和群测点,都不得自行发布地震预报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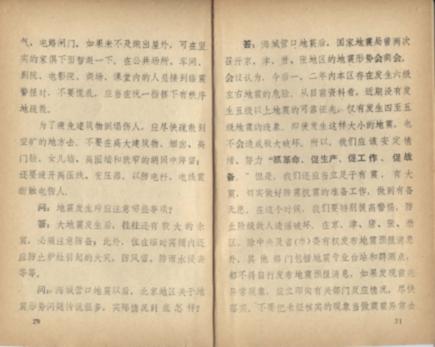
(图7:父亲遗物中的印刷体资料)
“唐山地处京津唐地区,首都北京近在咫尺。当时要在京津唐地区提5级地震预报意见,那是冒很大风险的。”黄相宁(原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华北三队,唐山地震后曾受华国锋召见)后来回忆时这么说。
在1976年初前后,四川龙门山汶川一带发现有明显的地震异常,当时引起了地震工作者们的强烈关注,他们推断这一带地下可能孕育着一场大震, 可是这场大震会潜伏多久是个未知数,是几个月、几年、还是几十年?后来当地出现了小震,风吹草动,上级部门在1976年6月中旬发布出了龙门山汶川一带的六级地震预报。据说,消息发布后引发了社会动荡,造成了人们恐慌,可是,过了一个月地震也没有动静,中央责成国家地震局出面解决,国家地震局作为一个没有行政职能的科研机构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唐山地震过后的8月16日,四川的松潘和平武相继发生了7.2级地震,距离30多年后的汶川地震震中映秀镇有200多公里,松潘、平武与汶川分属不同的地震带,松潘、平武地震是否对应了1976年初传说中的龙门山汶川地震异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系到首都圈的地震预报非同小可。当时“京津唐渤张”的地震预报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查志远深知当时地震预报科学的真实水平,可又骑虎难下,他后来表示当初有一肚子苦衷:“预报一次五级以上的地震,就得上报到中央国务院,这可是惊动中央的大动作,一旦把整个‘京师’地区闹了个惊天动地,碰巧预报准了固然皆大欢喜,如果错了呢?如果根本没有发生地震怎么收场?谁来收场?”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京津(唐渤张)大震要求成功预报?!
预报地震三要素:时间、地点和震级。三要素之中时间是最难判断的。地震,号称科学界的”癌症”,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准确预报大震,别说精确到一个月,就是精确到年都困难。
国外曾有评论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地震工作者不知天高地厚,蚂蚁啃骨头般地钻研着地球震动预报技术。这种说法也无可非议,当时的中国地震预报事业处于一个巅峰时期,各地的地震工作者们为了提高预报准确性可说是心力交瘁、呕心沥血。(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地震预报回归现实,地震预报科学重新定位回了探索阶段的初级阶段。)
“小震闹,大震到”,这是海城地震的核心经验,海城地震的经验最后升华成了这六个字。当时国家地震局为了推广这一经验,曾印制了大量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小震闹,大震到,地震一多一少要报告”。这些海报分发到了全国地震系统的各个基层单位。
海城之前的邢台地震就是小震闹后大震到。邢台地震发生于1966年,震级7.2级。邢台地震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地震预报意识,也没有地震局,邢台地震造成了8千多人死亡,3万多人重伤。
海城地震与邢台地震同出一辙。海城地震预报结果成功,但过程并非完美。海城地震发生于1975年2月4日,1月15日海城地区开始出现小震,大震前三天小震活动突然增多,大震前一晚小震频繁震了一夜,完完全全是一个邢台地震的翻版。几乎所有地震工作者都发出了呼吁,国家地震局半夜0时30分上报地震预报意见。凌晨的时候,海城地区又出现了一个5级左右的地震,一些烟囱被震倒了,大多数老百姓跑出家门。上级领导部门上午经过研究决定,同意发布地震预报。上午10时30分地震预报以辽宁省委的名义正式发出,晚上19时36分大震来临,海城临震预报获得成功。
海城地震震级7.3级,震源深度16公里,震中烈度9度,死亡1千多人。
梅世蓉在2006年谈到唐山地震时,她遗憾地说:“小地震这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承认,这是一个可靠的前兆。可是唐山…”。唐山,在唐山,直到大震发生前一秒,小震都没撞上来。
纵览邢台地震、海城地震和唐山地震,从技术层面上讲,海城地震的核心经验不仅是中外地震史上“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典范,而且,还演绎成了”成功是失败之母”的典范。
然而,奋战在第一线的地震工作者们并没有认同完全依赖小震的观点,许多地震工作者包括基层台站的工作人员都在全力以赴、兢兢业业忘我地寻找着地震来临的蛛丝马迹,尽管一些地震异常忽隐忽现、稍纵即逝。
曾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陈颙回忆时说:“当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河北省地震局和原北京地震队的部分同志都曾察觉到京津唐地区孕育着比较大的地震危险,也看到了某些异常,并且积极地落实核查。”
1976年7月27日,唐山地震前一天。唐山气候一反常态,结束了一个多月以来的阴霾多雨天气,迎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早晨,河北省地震局赴唐滦六人小组再次前往昌黎地震台,一路上阳光普照。
(九)大震来临
1976年7月27日下午,六人小组从昌黎又返回唐山,昌黎地电有异常。路途中,他们还曾去了二区测队一分队。下午期间,我的父亲曾给河北省地震局打过长途电话,当时局里主要领导们都到市里开会去了,会议地点是在石家庄市委招待所。曾有其他领导接电话说要总结三天,需提交详细书面报告。
梅世蓉在2006年回答新浪网友提出的关于唐山地震预报问题时,她讲到了当时地震系统内部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她说:“是有些预报,但是报了京西北,延庆、淮南、张家口一直到内蒙,也有报京西南,甚至报的保定,当然也报北京了,还有报唐山、滦县这一带,报一大片,当时预报意见,向局领导汇报以后,领导觉得你们汇报这一大片我们怎么措施?”
7月27日晚上,坚持唐山和滦县这一带的六人小组入住在附近的一个招待所,这个招待所的电灯比较明亮。晚上的时候,我的父亲等又出去拨打长途电话,再次拨通了河北省地震局的值班室,值班室人员跑去宿舍叫来了分析预报室主任等……
谢美娟(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地磁组,退休后移居美国)后来回忆时说,地震地质赴唐滦小组当时急着向局里作汇报。
六人小组最后获准第二天返回石家庄进行详细汇报,具体从唐山返程的时间定在了7月28日早晨6点。
刘占武后来回忆说,根据考察结果,他们地震地质调查组发现的情况有很多。他还说,苏英俊是带队的,老资格的大学生,贾云年也是学的地球物理,中国科技大学毕业,他们地震地质调查组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他们临走的这天,他们跟唐山地震队领导交流了情况,他们讲到了异常,意识到了有新的活动,他们要立刻回去汇报。
王运启(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水化组,后曾任法规处处长)后来回忆说,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六位同志专程来唐山进行地震地质考察,到7月27日他们已经完成了全部的野外工作准备返回石家庄,熟料,地震来得如此迅猛……
7月27日夜里,唐山天气闷热,这个夜里不知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是怎样度过的。后半夜,唐山天气骤变,出现间歇阵雨,有雷电触及地面,仿佛点燃了唐山大震的引信。父亲,父亲,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地震走到你们前面去了。
7月28日,凌晨,准确时间是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秒,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爆发了。
……
(十)全军覆没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候,石家庄也剧烈摇晃了一下。那个凌晨,我被母亲喊醒说地震了赶快下楼,一家人惊慌失措就往外跑。当时楼道里和外面都有人在喊“地震啦,地震啦”。
我家住的是地震局宿舍,大人们几乎都是地震局的职工。当时冲下楼的时候,只见那些大人们推上自行车就往外面的马路上跑,衣冠也不整,边跑边跨上自行车,直奔地震局办公楼。
河北省地震局的相关人员在局值班室集合,时任河北省地震局局长刘长垣现场指挥,他心里明白,地震应该来自唐山,地震地质组的人曾经坚持说过多次了,当初应该相信他们来着,如果地震不是发生在唐山,就是又被地震给愚弄了,如果真是发生在唐山,现在悔恨也来不及了。刘长垣命令值班室人员立刻与唐山联系,并让通知我父亲,让他们六个人早上6点不要往回赶了,要继续驻守唐山,坚守岗位,听从指挥。后来,刘长垣就被河北省省委的人叫走了。
值班员们用所有的电话拨打唐山,可是拨往唐山的电话都没有信号,他们继续拨打电话,一遍又一遍,就是没有信号。那个时候,所有与唐山的通讯都中断了。
一个多小时之后,大约凌晨5点左右,省地震局从河北军区得到证实,说是河北军区收到了唐山附近驻扎部队用无线短波电台发回的信号,内容说唐山方向望过去是空的了,城市不见了。
……

(图8:唐山震后远景,城市夷为平地)

(图9:唐山煤矿工人宿舍)

(图10:唐山地委办公楼)

(图11:唐山开滦煤矿招待所)

(图12:唐山第十中学)

(图13:唐山市郊)

(图14:唐山居民楼,图片来源王二)

(图15:唐山幸存者,孤苦伶仃了,掩饰不住的悲伤)
当天的傍晚,7月28日18点45分,父亲等六人在一周前刚刚去过的距离唐山市40公里的滦县也震了,震级7.1级。位于滦县的滦河大桥,号称连接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在这次的地震中彻底垮掉了。

(图16:滦县滦河大桥)
我的父亲和地震地质组赴唐山的同事们这天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三天后还是没有回来,后来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苏英俊,40岁;贾云年,33岁;黄钟,41岁;周士久,23岁;王素吉,29岁;阎栓正,37岁。
……

(图17:河北省地震局赴唐滦六人小组成员从左至右:苏英俊(组长)、贾云年、黄钟、周士久、王素吉、阎栓正)
(十一)接应六人小组
唐山地震的当天早上,河北省地震局就开始组织工作队赶往唐山。
时任河北省地震局副局长苗良田陪同省委领导乘坐飞机当天飞往唐山了解灾情。7月29日,苗良田陪同省委领导路过极震区时,他抽空儿跑去六人小组居住的地方看了看,那里的房子全部坍塌了,周围环境出奇的安静,也看不到解放军战士。据说那个地方是震中的震中,虽然救灾的解放军指战员们接到命令就立即开赴唐山,可是整个唐山城市都在等待着营救,参加救援的解放军每前进一步都能听到有人呼唤着救命,一路上哀号般的呼救声此起彼伏。苗良田曾尝试挪动预制板,可是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预制板连动都不动。由于时间紧迫,不能久留,苗良田眼看着昔日一同工作过的战友们被埋压在墙梁下面却爱莫能助,毕竟他工作重任在身。
河北省地震局内,一批又一批的工作队前往唐山监测震情。地形变组、地电组、地磁组、重力组、水化学组、水位组、地应力组和测震组全都出动了。说震情是命令,地震更是命令。
7月29日下午,河北省地震局在震后第一次接到了来自唐山的电话。唐山地区地震队副队长孟祥振在唐山机场的抗震救灾指挥部打来电话,他报告了唐山地震的灾情,并提到了来自省局地震地质组的六个人,说这几个人全被压在了下面,生死不明。另外,孟祥振还说唐山地区地震队的职工石蕴璇、刘信、傅长河和宋保田等已经确认遇难,还有不少家属也惨遭不幸。
傍晚的时候,我父亲的好友陈拴群,还有我家的对门邻居孙勇泉(原河北省地震局后勤组),他们打听到派往唐山的工作队都是去建立流动台、监测震情的,于是急忙打报告要求去唐山接应我父亲等六人。时任河北省地震局领导层成员王益海(曾任后勤组组长)立刻想了办法,他亲自跑去车队把当晚即将出发的第N批赴唐工作队专车内的空间重新布置了一番,在车里面又挤出一块空间,勉强能多蹲下两个大人。这样陈拴群和孙勇泉也搭上了赴唐工作队的汽车。
陈拴群是我父亲的同学,也是学地球物理的,他是在1974年2月从四川省地质局调往河北省地震队的。在1975年的时候,陈拴群曾和我的父亲去张家口调查过那里的震情,另外他还和我的父亲一起去过国家地震局搜集华北地区的地震地质资料。
说到张家口,就是指的“京津唐渤张”中的“张”,也是华北区域的地震危险区。1975年,我的父亲至少两次到张家口搜集资料,其中一次是和陈绍绪(曾任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任)一起去的。此外,父亲和地震地质组的同事们还去过邯郸、沧州、承德以及邻省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和辽宁等地做过调研,最后,地震地质组把目标集中瞄向了唐山。
陈拴群和孙勇泉所乘坐的汽车7月29日连夜北上。
7月30日一早,他们从北京再转去了唐山。据他们后来描述,当时唐山已是楼平桥断,一路上景像惨不忍睹,一座城市瘫卧在了地面上,登在高处,一望无际。他们先找到陡河,然后沿陡河一路下去寻找胜利桥,他们知道六人小组就住在胜利桥附近不远的地方。

(图18:唐山胜利桥)
花费了很长时间之后他们才赶到六人小组居住的地方,那里已是一片砖石瓦砾,四周到处都是陷坑裂缝,附近的桥梁也塌陷了,有几棵树孤零零地斜立着,空中游离着无数飞虫。

(图19:父亲等六人殉职的地方,一片砖石瓦砾,图中右侧是后来搭建的防震棚,图片来源河北省地震局)
陈拴群迫不及待爬在瓦砾上高喊 “苏英俊……苏英俊……”,没有回音,他向着各个缝隙里喊,也没有回音。陈拴群他们又喊“贾云年,黄钟……”,一个一个的喊,都没有回音。这个时候司机蒋忠义也赶来帮忙,几个人一起搬挪着上面的墙板,到天黑也没能搬开。
这个地方是唐山地震的极震区,震源深度10公里,地面地震烈度11度强(11+)。
地震震级是根据地震释放能量划分的,而地震烈度是用来衡量地面受破坏程度的,烈度共分12度。同一个地震只有一个震级,根据震源深浅和距震中的远近,地面上不同地区,其烈度大小是不一样的。距离震源近,烈度就高;距离震源远,烈度就低。烈度3度,人有感觉;4度和5度,吊灯明显摆动;6度,器皿倾倒,房屋受破坏;7度和8度,地面会出现裂缝,房屋受到严重破坏;9度和10度,房屋倒塌;11度和12度,地面上的一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陈拴群等几个人一夜守候在那里,他们说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许能听到我父亲他们的呼唤声。
7月31日早晨,太阳照常升起。上午的时候,他们突然看见远处出现了救援的解放军战士。解放军来了!解放军终于开进来了!有一个班的队伍跑过来,二话没说就直接投入了挖掘工作。

(图20:唐山解放路商业服务楼附近,六人小组曾在这个地点驻扎了几天,图片来源河北省地震局)
(十二)父亲的消息
在7月28日唐山地震的当天,哥哥和我曾到河北省地震局打听父亲的消息。当时,地震局的人都在紧张地忙碌着,根本无暇顾及我们。一位阿姨冲着我们匆匆地说了句:“唐山电话打不通,等有了消息,局里会通知你们家的。”
8月份了,我们家一直没有得到父亲的任何消息,母亲急得生病躺在了床上。
8月2日,星期一了,还是没有父亲的消息。哥哥和我又到地震局打听。当时省地震局的人都知道了地震地质组赴唐滦的六个人是回不来了,可是他们不忍心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我们,见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是停止说话,望望我俩,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
哥哥和我径直跑到地震局办公楼里,见到楼里的人都在忙碌着。我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向里探探头,看看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叔叔或阿姨。
河北省地震局的两座办公楼里在那些天里昼夜都是灯火通明,职工们也没有下班的概念,基本上总呆在单位,两座楼之间总能看到有人来回攒动着。地震局大门外的街道旁搭满了防震棚,没有一个是地震局的,附近居民们晚上都是睡在外面。或许是职业的原因,或许是其它的原因,地震局的职工们一直都是在楼里工作。
在一间办公室,我们看到一个人躺在一张钢丝床上,打着点滴,怪怪的。仔细一瞧,是我家邻居侯立臣伯伯,他的一只手拿着资料在和别人商讨问题。后来听人说,由于唐山地震的巨大压力,侯伯伯急得犯病了,他没有去医院住院,而是干脆把单位办公室改成了病房,这样边治疗边工作。
哥哥和我没有进去打扰,又继续在办公楼的楼道里转悠。在另一间办公室里看到了我父亲的好友李钦祖叔叔。他看见我俩,从房间走出来,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李钦祖是地震地质组的成员,他和我父亲同年同月出生,平时他俩在一起总喜欢探讨震情问题。在唐山地震之前,李钦祖曾和我父亲到河北磁县(历史上曾发生过7.5级地震)调查过唐山—河间—磁县地震构造带活动情况。这次地震地质组去唐山勘察,李钦祖当时患病住院了,组里就没安排他去。(唐山地震过去一段时间后,李钦祖作为地震地质组的幸存者,从普通组员直接跳升任河北省地震局局长。)
李钦祖叔叔走到我们面前,嘴角动了动,没发出声来。我们见他一脸憔悴,整个眼圈发黑,恍恍惚惚的,也不好多问。旁边有人过来告诉我们说,唐山地震发生后李钦祖一直没有离开过分析预报室这座楼,他每天独自呆在这个地震地质组的办公室里,现在这间办公室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妻子每天给他送饭他也不吃,都几天几夜了。
我跟着哥哥继续在地震局办公楼里跑来跑去,一层又一层来回转。楼道里有人提示我们,说这事儿有关部门知道情况,你俩应该找他们问问。在1976年前我家就住在这个地震局办公楼第三层,当时办公宿舍混在一起,放学后我常和儿时玩伴在这个楼里玩捉迷藏游戏,哥哥和我对这里的每个角落和各个部门所在的楼层位置了如指掌,可是从来不知道“有关部门”在哪里。
8月3日,我的叔叔也从老家赶来了,他和哥哥又到地震局打听父亲的下落。下午的时候,他俩回家来了,说是碰到了我父亲的老同学赵喜柱,他安慰了他俩(没有直接说明我父亲的情况),并带着他俩去找局长了,由于当时局长们正在开会,局长办公室的人让他俩回家先等着,说局领导开完会就会派人来我家。
说着说着,就有人敲门了。打开门一看,是地震局行政副局长李向前和政工组的刘慧英等。当时看到李向前的两只眼睛红肿着,白眼球里布满了血丝,有些吓人。我们知道情况不妙,本来都想好了见到他们后如何询问我父亲的情况,可是这个阵势,准备好的词语一下子全忘了。
他们进门后先是问候一番,表示局领导对赴唐考察同志们的家属非常关心,但由于局里工作太忙一直没能抽出时间来家里探望。
我忘记了是我母亲还是我哥哥对他们说,其实我父亲去了唐山后,地震局的人对我家都很关照,经常有人来问候、来帮忙,有父亲的同事,也有邻居,前几天王树欣(我父亲的同学,原河北省地震局职工)刚来过,他还推着小车去煤店帮我家把蜂窝煤买回来了。另外他们还谈到,我家楼下邻居胡长和(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综合组成员)很多次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后都先来我家,把买来的菜分给我家一半。
他们说了一会儿,可是没有提到我父亲目前在唐山的状况。后来,李向前迟疑了一下,说楼下有车等着,要把家属接到地震局,说局里还有领导要和家属见面。当时我的母亲身体不好,在床上斜躺着,李向前说让我母亲在家休息就先不要去了。
我们来到地震局后,被安排在二楼的会议室,工作人员搬来了皮椅子让坐下,然后又给沏上了茶水。过了一会儿,刘慧英让我们到李向前的办公室。
“你父亲是一名优秀的地震工作者……” 是李向前宣布的消息。说完第一句话后感觉他停顿了很长时间才讲出下一句:“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们的父亲在唐山殉职了……”
虽然心里已经有了准备,但是在被证实的那一刻,也是撕心裂肺般的悲痛。小时候在电影里见过这样的镜头,没想到现在轮到自己了。
(十三)生死的界限
后来我家了解到,父亲他们六个人是在唐山震后第四天的中午被挖出来的,挖掘的时候有河北省地震局的人员在场。他们说六人小组遇难的地点是唐山地震震中的震中,那个地方在唐山市的路南区,震源就在他们正下方的十公里处。
地震局的人说,从挖掘现场看,我父亲和贾云年、黄钟住的房间到处都是散落的纸张,那天晚上他们有可能在房间里整理资料,领导已经批准他们第二天可以返回省局了,并定好28日一早从唐山返回石家庄后进行详细汇报。
地震局的人还说,六人小组在唐山期间先后驻扎过几个不同的地方,最后几天他们驻扎的地点落在了极震点的位置上。27日晚上他们入住了附近的唐山地区农科所的招待所,招待所有两排房子,房子是水泥预制板结构,地震的时候所有的房子全部倒塌,只有半堵墙立着。
地震局的人又说,我的父亲是在一面墙的下面被发现的,墙被一个硬物支撑着,下面有一定的空间,父亲躲在了那里,父亲的身体一点外伤都没有,鼻子和嘴里有土,像是后来窒息而死,如果救援早两天,说不定还能救活。
生死的界限是如此的脆薄。
我一直都不敢想象父亲在生命最后弥留之际的悲惨处境,但是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死不瞑目,为了预报出华北区域大震,父亲和地震地质组的人竭尽全力,他们的目标锁定范围逐渐缩小,在唐山震前一个多月,父亲带领手下组里几乎所有的成员义无反顾,直奔唐山。可是,到头来前功尽弃,所有努力全部付之东流,而且,最后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和唐山一起毁灭。
如果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并非无所不能。纵然有千悔万憾,时间上一旦发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神也无法改变这个已有世界的时间单向流失机制。
我知道描述当时的一幕是残忍的,我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合适的记录者,无论语言还是文字也都不是我的擅长,可是那毕竟是曾经的真实。
那个晚上,我的父亲和贾云年、黄钟住在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三张床,父亲和贾云年的床位是里面的两个,黄钟的床位靠近门口。
我父亲的情况在上面说过了。
贾云年是在床下角落里被发现的。他的床被砸断,当时他已经躲在了床下,裹着被子紧靠着墙根。他的头部有被断床螺丝钉划伤的痕迹,他身上的其它部位没有任何伤痕。据在场的人员讲,他被闷在了里面,动弹不得,那里不见光明,没有足够的空气。
黄钟的床离门出口只有两步距离,当时他正在往外跑,一只脚已经踏出门外,房顶门框砸了下来,把他卡在了那里。解放军战士们挖开的时候,只见他的手中紧紧地抓着一只布绒娃娃,那是买给幼小女儿的礼物,他已经答应小女儿多次了,可是心愿始终未了。
阎栓正住在另一个房间。从现场看,他也躲在了床下, 床的一端被房顶上的一个板子砸下去了,床的另一端翘了起来。不幸的是他的头部是在床被砸下去的那一端,可以看到他头上的伤痕,头部下方的地上有血迹。
周士久被发现的时候,身上还裹着蚊帐,他不在床上,也不在床下。从挖掘现场判断,他是在蚊帐里刹那间直接往门外冲的。地震局的人说这个小伙子反应很敏捷,人都快要冲出门口了,可是,不知是蚊帐被挂住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最后还是被倒下的墙压趴在地上。地震局的人还说,当时六人小组所处在的那个极震点位置从地震发生到屋顶落地,最多也就是几秒种的时间。
王素吉一人住一个房间,当时她是躲在了桌子下面,一边的桌腿被砸断,另一边的桌腿还支撑着。她就蹲在这个有桌腿支撑着的这边,有足够的空间,她的身体没有受伤。当救援人员把桌子上方支着的板子挪开时,她还在那里蹲着,一动不动。陈拴群把手靠近她的嘴巴和鼻子,感觉不到呼吸,也感受不到热量,再试试脉搏,已经不跳动了。孙勇泉判断说她曾坚持过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没能等到救援队伍的到来。他还说,王素吉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的姑娘分配到省地震局后,一直都希望学以致用,将学到的课本知识用于实践。
这天是唐山地震后的第四天,80多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据在现场的人员讲,解放军指战员们没有太多的挖掘工具,只有几把铁锨,当时都是抱着万一有生还的希望,所以基本上没使用挖掘工具。他们主要是用手扒,用手拽,用手抠,有时一起抬,一起扛,他们的嗓子都喊得哑了。这些解放军战士几乎手上都有伤,有的胳膊或腿上还扎着绷带,整个过程他们没有片刻的休息,挖掘完后他们跑着步就去别的地方了。据说这个班的解放军战士来自沈阳部队,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有留下姓名。
经历过唐山地震的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抗震的解放军战士们,他们是冒着余震的危险,不顾个人安危,奋不顾身抢救落难的生命。救援的解放军战士们大多数都负了伤,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

(图21:抗震救灾中的解放军战士)
六人小组成员们曾被安葬在了附近的一条河沟里,后来为了预防瘟疫发生,上级命令必须把已掩埋的尸体全部转移到郊外的地方。这样,和大多数唐山地震遇难者一样,他们经历了两次的从地上向地下的穿越。
最后父亲等六人被运到了唐山东部的一个丛林里。丛林里南北向挖了一条长长的土沟,他们每人都被装在了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内,扎上口,然后放入在土沟深处。从南向北依次摆放的是黄钟、苏英俊、王素吉、贾云年、周士久和阎栓正。
刚要填土的时候,陈拴群突然又跳进土沟里,他把装有我父亲的白色塑料袋打开,然后把我父亲的工作证放了进去,并小心翼翼地搁在了我父亲的头下。陈拴群说我父亲生前一心想着预报地震,现在死在了唐山,就让他的工作证陪伴着他吧。
然后,陈拴群又把一个铝制饭盒放进了装有黄钟的塑料袋子,他说,地震地质组这几个人在唐山的一个多月里,每人都携带着一个铝制饭盒,每天在野外的奔波途中都是靠它填肚子的,黄钟的饭盒上刻有名字。
孙勇泉在土沟的旁边跪在地上一声不吭,他默默地在为六人小组每名成员钉着形状各异的木橛子,当作是他们的墓碑。他后来曾回忆说,在唐山那段惨痛悲凄的日子里,他眼前总是看到一排排的翻斗车在小路上开来开去,随后又是推土机推来推去。
那条沟究竟有多长?最后总共到底埋了多少人?在场的人都说不知道。
后来听媒体讲,面对这场毁灭性的灾难,我国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了困难,最后夺取了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
哥哥和我后来去看望现在已经退休的陈拴群叔叔和孙勇泉叔叔,当谈起唐山地震时,孙勇泉仍还心有余悸。他说,这三十多年来一直害怕见到翻斗车和推土机,每次看到翻斗车在路上行驶,他心里总是想着那个翻斗里装着的是死人,每次他看见推土机出入工地,他总是感觉那个推土机正准备去掩埋尸体。
(十四)怀念父亲
少年丧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在得知父亲殉职的那些天里,我天天去到父亲工作过的河北省地震局大门外,在那里漫步、徘徊。当时的河北省地震局位于石家庄市范西路22号,地震局的主楼是一座拐角的三层楼,主楼的东边是一座两层的东西向小楼,这座二层的小楼就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小楼二层楼道南侧正对楼梯的房间就是父亲的办公室。地震局的大门是用铁栅栏做的,从大门外一眼就可以望到分析预报室那座小楼的门口。
记得以前我放学后常常到那儿附近玩耍,有时候等待父亲下班后一起回家。父亲在到下班时间后经常不能按时出来,我总是要等一段时间,几乎每次都是父亲最后一个从分析预报室小楼走出来。有时我在外面要等很长很长的时间,可是无论等待多久,父亲最后总会走出分析预报室小楼,然后推上自行车,驮我回家。
唐山地震的那段时间里正值学校暑假,傍晚时分,我总是又站回原来等父亲的位置,天还是一样的天,地也是一样的地。我依然从地震局大门外向里张望,地震局院内和以前没什么两样,父亲的自行车依旧还停放在分析预报室楼口的北侧,只是倒在了地上。我望着分析预报室的楼门口,我的父亲再也不能出入这个分析预报室的小楼了。我知道奇迹不会出现,可是我还是忍不住盯着分析预报室的楼门口,仔细打量着从里面走出来的每一个人的脸孔……
在那些日子里,省地震局大门外总是集结着一批人,他们焦灼、忧虑,还带着愤怒,更多的是悲伤和无奈。看他们那种样子,可以肯定,他们一定是有亲友在唐山。一天下午,我看到地震局大门口集结的人越来越多,前面的人抓着大门的铁栏杆对里面喊叫着,还有人往里面扔砖头。地震局的大门被一个铁链子紧紧地锁着,地震局内部人员的出入都是不露声色悄悄地走西侧那扇小门。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收发室值班人员走过去在大门内侧隔着铁栅栏对他们解释着什么,可是他们仍然还是叫嚷着。后来,看到前面有人从人群里开始撤出来,边撤边对后面的人说:“他们地震局勘察队的人也在唐山被砸死了,连他们勘察队的队长都死了,大家还是回家吧。”一些人开始散去,有的人嘴里嘟囔着:“这些该死的!”
我站在人群的后面,心像被针扎一样,默不作声,低下头,然后又仰起头,望着天,这样眼泪不会掉下来。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