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换一张面孔 信仰着并生活着
南方周末 作者: 南香红/
编者按:乌鲁木齐“7·5”事件让人们对中国西北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充满了关注。这是怎样的一个地区?它的性格、它的特殊性是怎样形成的?从大历史与大背景的角度,或许能给读者一些启发。
许多人都说新疆是一个“谜”。
尽管这种说法显得有点陈词滥调,但是,新疆的确是让人眩惑的。
绵延的雪山、茫茫的戈壁、无垠的沙海、星星点点的绿洲。最高和最低、最冷和最热、最彻底的荒凉和最充裕的富足,都在她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一呈现。从沟沟有黄金的阿尔泰山,一下跌入荒凉的准噶尔盆地;从上可扪天摘星的天山,再次落入塔里木的茫茫沙海;从喀喇昆仑山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到吐鲁番盆地海平面以下154米的艾丁湖,新疆这种一落千丈、大起大落的地理变化,有一种惊险的美丽。
如果属于自然的东西还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几千年的新疆所变幻出的文明色彩足以让人眩晕。
新疆是世界上少有的文明交汇与混杂之地,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埃及和两河文明,古老的佛教的石窟、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古希腊罗马的有翼天使,不知道有多少民族多少文明在这里一一飘过,一个文明覆盖了另一个文明,一个民族吸纳了另一个民族。现在的新疆仍有13个世居民族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
新疆是个体的生命很难穷尽的地方,真实的新疆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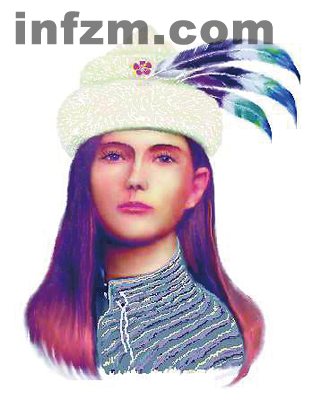
在新疆发现的孔雀河“楼兰美女”,让学富五车的专家们惊讶得长时间无语。

楼兰

艾提尕尔清真寺

乌鲁木齐大巴扎

喀什一角
【一】一千年换一张面孔
有一句话说,如果到了新疆而没有去喀什,就等于白来新疆。
喀什是新疆最让人沉迷的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喀什的色彩就是新疆的色彩,而喀什色彩中最浓烈的一笔就是宗教。
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喀什不会变,因为喀什的中心不会变,而喀什永远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艾提尕尔清真大寺。
喀什是世界上少有的围绕着一座清真寺而运转的城市,它的商业、街市、全部的市井生活都是艾提尕尔塑造和改变的,每天,这座城市随着艾提尕尔的呼喊被唤醒,夜晚整座城市又在艾提尕尔的祷告声中睡去。“安塞拉甫——哈依鲁木比乃——那吾来——”(“沉溺于睡眠的人们啊,快点起来吧,快点起来做礼拜吧……”)
一声悠长、悠长的呼喊从艾提尕尔的高高的宣礼塔上响起。喀什噶尔还在沉沉地睡着。冬天的早晨寒冷而黑暗,粘稠空气沉重地压在城市的上空,这呼喊一波一波地冲开夜的迷障,盘桓在大街小巷和沉睡的人们的枕边。
喀什人听到了这声音,便在黑暗中起了身。房间里很寒冷,夜里炉火熄灭了。他们用很冷的水洗脸,然后出了门。
喀什的街上,夜气还没散尽。影影绰绰中,细如蛛网的小巷的巷口吐出很多人,汇集到了有路灯的大街上,人们并不言语,就像是依然在梦中一样,向着那声召唤发出的地方游走。
千百年来的每一个早晨,喀什都是这样醒来的。她不是因为天光而醒,不是因为鸟虫鸡鸣而醒,而是因为这样的一声声的召唤而醒。城中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维吾尔人、汉族人、塔吉克人、俄罗斯人、柯尔克孜人、乌孜别克人都在这呼唤中醒来,这呼唤已经在他们的心里沉淀下来,变成一种不需要等待的预约,也从来都不会失约。
不仅是喀什,乌鲁木齐的每一个早晨,也是在这样的呼唤中醒来。尽管乌鲁木齐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一个国际口岸,但这座城市的一个部分还是保留着它的传统。从南门向南,阿訇是这里起得最早的人。他每天站在高高的清真寺穹顶上,喊醒沉睡的人们,喊醒这座城市。而乌鲁木齐的另一半,南门以北的人,非穆斯林们,此时拥被高卧,好梦正酣。
我曾在喀什遇到了三次穆斯林的肉孜节(开斋节),这是喀什情绪最饱满的时刻,对于伊斯兰的教民们来说,已经等待了整整一个月。
这就是斋月——是伊斯兰教徒的必行的修行功之一。伊斯兰教历的9月,教徒们天一放亮便禁食禁水禁房事,到了晚上太阳下山之后,才可以进食。一个月过去,当新月再次升起,斋戒结束,这就是开斋节。
情绪在黑暗的黎明就开始酝酿,人们在黑暗中起身,然后静默地等待艾提尕尔的召唤。喀什周边方圆四五十公里甚至更远地方的穆斯林早已在半夜里起身,汽车、卡车、拖拉机,更多的是毛驴车,通向喀什的大路小道都充满着星夜兼程奔向喀什的人们,在冬天寒冷而黑暗的晨霭中,人们被一种力量吸引,向着一个方向,不言不语地赶路、赶路。
对于喀什,艾提尕尔是一个充满魔力的中心。艾提尕尔牵动着喀什的每一根神经,甚至牵动中亚和整个世界的神经。
这是新疆伊斯兰宗教气氛最浓厚的地方,从喀什扩散开来,往乌鲁木齐,往新疆的其他地方,宗教气氛就或浓或淡,深浅不一了。
宗教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新疆,这一点从生活的每一处都可以体会到。比如斋月期间的喀什,所有的清真餐馆都不开门,喀什成了一个禁绝炊烟的城市,街头只有几家零星的汉人餐馆开着门。而当节日祈祷一结束,艾提尕尔清真寺穹顶上的达甫鼓和唢呐响起,上万人开始在艾提尕尔广场上跳舞的那一刻,喀什的所有餐馆好像接到了一道命令,满城一瞬间处处饮烟,巷巷飘满了抓饭的香味。
现在新疆的色彩是伊斯兰的,但是,一千年前新疆的色彩是佛教的。一千年换一个容颜。一种文明覆盖了另外一种文明。但文明的覆盖并不能做到彻底,老文明的底色让新文明的色彩混杂而斑驳,因此新疆的颜色是混杂的。
1979年首度对塔克拉玛干沙漠楼兰地区的考察,发现了古墓沟太阳墓地和孔雀河“楼兰美女”。这两个发现让学富五车的专家们惊讶得长时间无语。让世界惊讶的是太阳墓里的人的人种,他们均属于欧洲原始白种人。而那个发现于孔雀河的“楼兰美女”也是白种人。
而后的小河墓地、洋海墓地、扎洪鲁克墓地等大型新疆早期墓地的考古发现,使一条规律显示出来:在距今3000年到4000年的时间段里,新疆所有的墓地考古发现的都是白种人。
这是一段不为专家学者所熟悉的历史,也更不为普通人所知道。但一个事实是明显的,新疆的人种来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来源和混杂的,那些曾经活跃于新疆沙漠草原间的白种民族虽然只留下一个背景,但却成为新疆民族组成的底色。
汉人对古称西域的新疆的了解来自于张骞的报告:“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这时新疆绿洲间已经进入了城邦农耕与畜牧并行的文明,黄种和白种杂合的人种出现在楼兰的古墓中。新疆已经在近二千年的时间维度上转换了一次容颜。
汉民族也就在这时进入了西域并定居下来。在新疆的13个民族中,汉人应该是最早并持续在新疆定居的民族之一,并且汉文史书也是在二千年的时间长度里持续地观察和记录新疆民族历史的变迁。对于这一方的历史,游牧民族没有记录,西方的记录是零星而不完整的。
公元644年的春天,唐玄奘翻过昆仑山回到了喀什。他在他的《大唐西域记》里记载了他看到的喀什:君臣百姓人人淳信佛法,有大小寺庙数百所,佛僧万人。
而当马可·波罗1271年来到喀什的时候,喀什已经信奉伊斯兰了。喀什给马可·波罗的强烈印象是到处是美丽的果园和葡萄园以及喀什人的经商意识,他说,“他们经商的足迹遍及全世界”。
新疆在另一个一千年的时间维度里再一次转换了容颜,她已经从佛教文明转成了伊斯兰教文明。
历史渐渐被现实所覆盖,但是总有一些东西会沉淀下来,嵌入新疆成为它的一种原色,一种格调。今天,当喀什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广场跳起节日舞蹈的时候,专家们会说那是萨满舞,因为维吾尔人历史上信奉过佛教也信奉过萨满教;而乌鲁木齐街头走过的那些高鼻深目蓝睛的人,暗示着一条绵延几千年时隐时现的血脉的流传;而在二道桥市场里的英吉沙刀具摊上弹剑细听,会听到一种大漠古风的啸音;还有从新疆和田民居的雕梁画栋上可以看到古希腊雕刻艺术的遗风;从克孜尔千佛洞的佛教壁画飞天的身姿上,可以看到印度佛教初次踏上西域大地的自信;而从南疆街头小抓饭馆里传出的十二木卡姆的丽音中,可以听出丝丝古代阿拉伯的忧郁……这些都是若有若无说不清道不白的,但都是属于新疆的意韵。
新疆并不单属于哪一个民族,它是多民族多文化的交融与汇合。
【二】信仰着并生活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集《多种文化的星球》指出:“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和宗教仪式,它提供了生活的指南、综合的原则和所有生活方面的规章制度——从人际的到国际的。”
艾提尕尔对周边地区及中亚、西亚的穆斯林的吸引是非凡的。据说,一个修行的人,如果能到这里作一次礼拜,其功德如同到麦加朝圣。
以一个记者,并且是女记者的身份,我提出了采访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的要求,我对采访被获准并不抱希望,但意外的是我两次都获得了准许。
2001年,我拜见的是沙迪克·卡热·阿吉,2006年我再进艾提尕尔的时候,得知沙迪克·卡热·阿吉已经去世了,主持艾提尕尔清真寺的是居玛·塔依尔大毛拉。
我在艾提尕尔清真寺一侧的一个小屋里见到了胸前飘着花白胡须,头上戴着很大很白的缠头的沙迪克·卡热·阿吉。老人紧闭着的嘴唇和没有情绪显露的脸使他身上有一种威严。
沙迪克·卡热·阿吉出生在一个宗教世家,在他的一生中,学木匠的时间几乎和他读经学院的时间一样长。他靠木匠的收入养活他的孩子和妻子,一直做到1983年。采访时,他靠政府的600元津贴生活。他是全国八、九届人大代表,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务理事,自治区伊斯兰协会副会长。
沙迪克·卡热·阿吉是艾提尕尔清真寺的主持阿荣汉·阿吉的继任者。1996年5月12日6点30分,七十多岁的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在前往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礼拜的路上遭到暗杀,两个蒙面人将阿荣汉·阿吉刺了21刀,将他的儿子刺了13刀。
阿荣汉·阿吉和他的儿子奇迹般地被救了过来。刺客也是伊斯兰教徒,在被审讯时他说,当时心里矛盾极了,他们被要求虔诚地忠于组织,要用生命保证完成任务,同时又因为阿荣汉·阿吉的宗教领袖身份而无法下手。
阿荣汉·阿吉是全国伊斯兰协会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新疆伊斯兰协会主席,对他的暗杀是一系列恐怖暗杀行动之一。
作为一个教徒为什么要刺杀自己的宗教领袖?有记者将这个问题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时,得到的回答是因为阿荣汉·阿吉在艾提尕尔清真寺里讲伊斯兰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反对暴力、恐怖和动乱,而这一点为新疆的三股势力之一的极端宗教势力所仇恨。
阿荣汉·阿吉在那次被刺之后身体受到重创,不再主持清真寺的工作,四年之后去世。
2006年我再访问艾提尕尔清真寺的时候,得知沙迪克·卡热·阿吉也去世了。新任的大主持是居玛·塔依尔大毛拉,他原来是喀什另一所清真寺的主持。
我拜见他还是在上一次的小房间里,居玛·塔依尔大毛拉身体瘦小,显得有点孱弱。像上次一样,老人见我进来,也是缓慢地从炕上站起,也是优雅地抚摸了一下胡须,让人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恍然感,然后他跪坐在土炕的地毯上,等待采访的开始。
居玛大毛拉告诉我,他的任职补贴提高到了每月760元,比去世的沙迪克·卡热·阿吉提高了160元。政府还为他配备了一辆桑塔纳2000汽车,并有专职的司机,因为每天早晨的礼拜要穿过喀什又黑又细的小巷子。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采访中,居玛大毛拉揣在长袍子中的手机响了,他摸索着从胸前掏出来。听得见里面是一个少女又尖又高的撒娇的声音,我猜想那可能是他的女儿。有趣的是,手机的铃声设定的是那声悠长的召唤:“安塞拉甫——哈依鲁木比乃——那吾来——”。
这个细节让我感觉和这个神秘威严的老人很接近。而我的感慨是,一个如此高位的宗教人士,却那么平俗而真实地生活着。
宗教本来是个人化的内心信仰和崇拜,是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之一,世界没有哪种宗教是教导人与社会为敌、以人类为敌的,除非是邪教。然而,“宗教极端势力”正是利用宗教为掩护非法活动,喀什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买买江·夏吾冬向我介绍,喀什曾经一度是非法宗教活动、暴力恐怖分子活动的重灾区,因此喀什总结出一些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的经验,比如少数民族干部联系清真寺,与宗教人士交朋友;不干预宗教内部事务等,这些经验被称为“喀什经验”。
在新疆的城市乡村,我看到了真正的宗教生活,它是纯净的、平和的、向善的。
65岁的阿不力孜·阿不都拉是喀什市的一个依玛木(宗教职位),他主持的清真寺是喀什815个清真寺中最小的一类——只能做每日五次的礼拜,不能做居玛日(星期五)和节日的礼拜。
阿不力孜·阿不都拉同时也是一个小商店主,他的生活一半是宗教的,一半是世俗的。每周除了周五之外,他要每天到清真寺里主持五次礼拜。天不亮起床,礼拜回来,打开小商店的窗户,生意就开始了。晚上,关上小商店的窗户,去主持最后一次礼拜,一天就结束了。
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穿行在艾提尕尔清真寺旁边的于木拉克希海巷里,过着最普通但是却是有信仰的生活。
信仰是人类心里的一种美好感情,对于许多教民来说,信仰更多地是个人内心的需求,信仰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我认识的阿木提·阿吉是喀什市一个经营毛布店商人。对他来说宗教在现实生活面前,已经大大地退让了。阿木提·阿吉从16岁自己独立开店,现在他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穿行在亚洲和欧洲大陆上,进行着他的国际贸易,但在宗教生活上,21岁的他已经可以在名字的后面加“阿吉”二字了,这说明他已经到麦加朝过圣了。
伊斯兰教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还是生活指南和生活原则,他奉行着宗教的训诫,不抽烟不喝酒。但他不一定每天五次礼拜都到清真寺里去做,因为大多数时间他奔波在经商的路上,但是,到了宗教节日这一天,他一定会到艾提尕尔清真寺去,这是一个必行的仪式。阿木提·阿吉是喀什许许多多伊斯兰教徒中的一个,他们信仰,并把生活和宗教安排得妥当均衡。
无论是高大的殿堂,还是简陋的小寺,信仰都在里面居住。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见过最纯净的信仰,不是在清真寺里,而是在沙漠人家插几根木棍分隔出来的一小块地方,在沙漠里是没有条件建一所真正的清真寺的,但一样有信仰留驻的洁净的地方;还有在罗布泊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子里,男人们进山放牧,村里留守的都是妇女,但这个女人村里有两个男人,一个是老阿訇,一个是年轻的山村教师。老阿訇负责从孩子接生、命名、结婚到一个人入土死亡的所有仪式,教师负责教育山村的孩子。每当这两个男人从村里走过,妇女们都会站起身来向他们行礼、鞠躬,因为这两个人的存在,这个山村充满了宁静和自满。
人类是会信仰的族群,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信仰,经过几千年的文明淘洗,宗教已经渐次走出了对政治、对法治、对人类生活的干预和控制,转而固守信仰,变得更加纯粹和洁净,这才是宗教的本意。
【三】商业背景下的改变与不变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新疆有两个词可以代替:遥远、偏僻。但新疆巴扎上的商人却不这样看。在他们眼里新疆是中国离欧洲最近的地方,他们只需要一转身,就能从新疆的任何一个巴扎出发,走遍中亚,走遍欧洲。
巴扎,就是市场、集市。在新疆,除了像乌鲁木齐这样的国际化大城市外,许多城乡还保留着古老的传统——人们在约定俗成的巴扎日聚集在一起,贸易和交流,而每一个相对独立的绿洲,都有自己的巴扎日。这种以巴扎日聚起世俗生活的传统源自于丝绸之路商业与贸易精神,而新疆现在最著名的两个大巴扎,一个是喀什的中亚市场,一个在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子。喀什的中亚市场还保持着定时一聚的传统,每周的星期日是它聚起上万商贩的时刻,而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子早已变成了一个常设的综合市场。
现在的乌鲁木齐没有保留下更多的历史,但二道桥子不同,乌鲁木齐建在一条漫流的河滩上,二道桥子就是架在这座河上的第二道桥,二道桥子的新疆风情在那个咬得很重的“子”上,当地人说二道桥三个字时像蜻蜓点水一样快速,而把“子”重重地咬住。新疆话特别多“子”,拉条子、烤包子、杏子梨子、洋缸子(妇女)、巴郎子(小男孩)。
二道桥子是一个水很深的地方,这里有国际富商,也有摆几元钱小摊的贩子;有呼风唤雨的英杰,也有沉滓污流。热比娅就是在二道桥子支一张木床摆地摊起家的,二道桥子到中亚国际市场,到身家2亿元的女首富,她只用了十年时间。
二道桥子已经不是原来的地摊市场了,一座颇具民族风情的大巴扎建立了起来,白天这里做着中国和世界的生意,晚上这里天天歌舞,演绎着新疆的民族文化和风情。乌鲁木齐这座城市就在这样的商业气氛催生下渐渐地变了,你会发现,乌鲁木齐在向两个方向变化,一方面更国际化,一方面更具民族风情。而这种变化在离乌鲁木齐两千多公里的喀什市场里也发生着。
无论是喀什的大巴扎还是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子里,那里的商贩不仅仅是一口流利的汉语,还会一口流利的英语,而这几年二道桥子又流行俄罗斯语,而专对商人开办的英语、俄语培训学校也形成了一个产业。
在喀什的香港巴扎做了13年金银首饰加工的买买提明江的中心在香港。他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看香港当天的黄金交易价格。买买提明江细长的手指迅速在计算器上跳动,不到一分钟,一长串美元兑换人民币换算之后,给出了我采访他那一天的黄金价格:香港当天的黄金是每克人民币151.9元,这一天他把他的名叫“艾外斯”的金银首饰店的黄金价格定在每克152元。
国际化让新疆的商人意识到民族化的商业意义,因此,无论是街头小餐馆还是大买卖,都在强调着民族特性。而国际化同时也是对民族化的挑战,其中的压力和考验并不只是一个民族面临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世界问题。
在喀什,一个“见过世面”的商人的选择是,让自己的孩子小学时读维吾尔学校,这样不致于后代不懂自己民族的文化,中学开始就读汉语学校,并做考出新疆到内地读大学的努力。喀什市二中,是喀什最好的中学,这个有6000学生的中学是很难进去的,而进入其中的少数民族学生个个都是成绩优异者,他们在这里和汉族同学一样埋头苦读。
门打开了,不光有出去的新疆商人,还有进来的中亚商人。巴基斯坦商人米斯巴扎提和妻子及孩子用旅游签证进入中国,从一名走商逐渐做大成为了坐商。他在喀什租了店辅,租了居住的房子,用夹杂着生硬维语的英语和客人讨价还价。“喀什是一个好市场,这里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他说。
米斯巴扎提将喀什的苹果、葡萄运往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市,将巴基斯坦的地毯、铜制工艺品、衣服运往喀什。1公斤喀什的葡萄运往拉合尔市刨去运费关税等所有费用后能挣1元钱;一块巴基斯坦小方毯在喀什也能挣到1元钱。而他明白,喀什的市场稳定对中亚市场起着怎样的决定性作用。如果喀什的葡萄、大米上涨一元钱,就会引起中亚各国市场的震动,而喀什的鸡蛋运到巴基斯坦每个可以买到9角钱,这几乎是喀什的一倍。如果把喀什最普通的铁钉、铁丝、电焊条等小五金发往战后的阿富汗,一个月就可以挣100万。而只要中亚的战火和恐怖事端稍有间歇,总有坚忍不拔的商人行走在这条古老的贸易大道上。
商业带来的裂变有表层的,也有看不见的深层次的。
朱明俊作为《新疆日报》的摄影记者,在他的镜头里,艾提尕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艾提尕尔广场,曾经是一个杂乱的小摊小贩的天堂。烤肉摊冒着浓烟;蒙面的妇女摆着几个染红了皮的鸡蛋卖;行乞者摇着“萨依冬”唱着歌……
艾提尕尔广场,还曾经是一张温暖宽阔的大“地毯”,白胡子的维吾尔老人半躺在艾提尕尔清真寺的墙根下,眯着眼睛晒太阳。广场中心有不大的花池,雕塑着几个极为写真的大红石榴——喀什人最喜爱的果实。
现在的艾提尕尔广场一律用淡棕红色的砖雕做出伊斯兰建筑的风格,蓝色的幕墙玻璃闪闪发光,整个广场设置了数个喷泉,地面全部用淡土色的砖贴过。这种装饰,和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市场风格遥相呼应,用现代和时尚解读着民族特色。
一个时代退潮了,它所携带的象征物也随之退去,艾提尕尔广场就如一个宽阔的胸膛,包容着一切。
和四周簇新的建筑相比,只有艾提尕尔清真寺看上去有点破旧,没有多大的变化。“其实,艾提尕尔清真寺也变了。”朱明俊又摇着头否定自己刚才的判断。“过去它会毫不犹豫地拒绝,现在它变得宽容了”。
维吾尔妇女原来也是禁止进入寺内的,现在当礼拜结束的时候,她们也能进到清真寺里,不仅如此,清真寺里还有了女性导游。过去,女性游客穿着无袖上衣和短裙是不能进入的,现在艾提尕尔工作人员准备了漂亮的艾得丽丝绸,将丝绸围成披肩和长裙,就能进寺参观了。每当进行礼拜的时候它都要清场,游人、妇女、孩子一天会几次被请出清真寺。这时候的艾提尕尔显示出它神性的庄严,一群群大胡子的男人们鱼贯而入。但是,二十分钟礼拜一结束,它立即是游客和商贩的。几个十来岁的小孩首先冲上艾提尕尔的台阶,用维吾尔语大声叫卖:“袜子,袜子,两元钱一双。”
商业的力量是强大而无形的,它有致命的消蚀能力;它在人们毫不察觉中生长,挑战着传统,在无形中改变着一切。而面对改变是要丢掉一些东西,还是守住一些东西,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也是需要智慧的选择。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1505/



